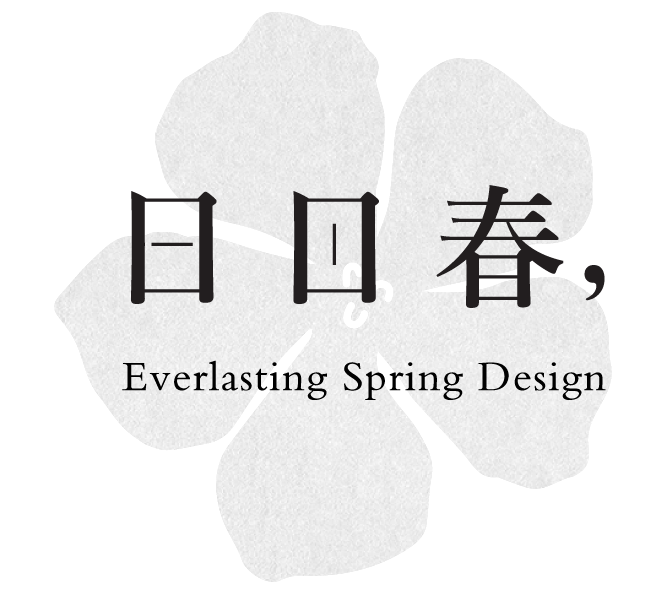文化化的自然:「人造/自然」綜合產製的混種後代

陸府生活美學教育基金會在近幾年持續關注土地、自然、海洋永續等議題,以永續與共生為理念的植森館中,為延續這項關注,在今年四月邀請策展人段存真策劃《人.造自然》一展。閱讀這檔展覽時,我認為它深刻的提出了當代社會環境的迫切提問:在人造世界與自然邊界漸漸模糊的當下,藝術與文化能否作為一種調和的語言,回應人與自然共治的時代?

展覽開幕策展人段存真導覽現場。
在此命題上,策展人段存真以「文化化的自然」作為本展作品選件的核心概念,鋪陳自然景觀在當代社會中的多重面向——自然如今在人類的社會中,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原野,而是可以透過人類的文化創造,使之被描繪、再現,甚至可以透過城市的生態需求,被製造與收編。在這樣的架構底下,「自然」作為一個主體,與人的關係不再是將我們視為「他者」(other),而是進入共生與共治的循環關係。策展人認為,當我們使用文化的眼光看待自然,會使我們感受到通過自然所喚醒的移情作用,因此這樣的自然不再是客觀的存在,而成為了我們再造出的「第二自然」。我想,《人.造自然》一展所創造的,並非囿於人干預、創造自然所產生的問題批判,而是在文化化的自然中,積極尋找對話空間的可能。

李光裕作品於陸府植森館展場。
以李光裕的雕塑為例,在他一貫的自然造型表象之下,展現的是宇宙星辰、自然萬物的生生不息,他透過植物的造型關照自身、關照心境;對自然造型的理解在他的作品中成為一種回應生活哲理的方式。同時,也是在這個過程中,產製出李光裕獨有的美學語境。而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呼應策展人在這次策展理念中,對藝術家創作的觀察所推敲出的理解——這些藝術家的創造,事實上是奠基於自然的敬畏、回應與轉化。

張庭溦於展場進行作品導覽介紹。
而藝術家張庭溦的繪畫,則是使用類似於膠彩「盛上」的技法,在畫面中堆疊過往作為城市建材材料的水泥,創造出流動山水般的色彩團塊。以工業材料描繪的自然,步步緊逼、挑戰觀眾對自然「有機」的想像;也更進一步地,將城市最常見的建材轉化為描繪自然意象的載體;使工業建材被文化化地將水泥叢林轉化為一處自然景觀幻象。如此這般,整體的觀看經驗便有如面前迎來一片人造、卻美麗的廣渺荒漠。這樣的創作,指向的是工業材料與自然景觀的交融,也是混種式地創造出屬於「第二自然」的人造景象。

陳肇驊,《島》,攝影:蔡青樺。

陳漢聲,《兩個太陽-菱角?芋頭?》(局部),攝影:蔡青樺。
另外,展覽中也呈現了多件以動力裝置與工業廢棄物製成的藝術作品,好比策展人在此次展覽委託陳肇驊所做的作品《島》,他使用廢棄的壓縮機作為動力材料,冷排使水凝結成冰於敲打成鯤身造型的銅板上,而熱排則使凝結的冰化為水氣,如雨水般的滋潤下面那塊生機勃勃的綠地,打造出人工與自然相互共生的生態循環裝置;而我也認為此作象徵性的表現出人造物與自然景觀綜合產製的混種後代,生動地演示「人.造自然」的當代關係。而陳漢聲則專注於高雄的水資源問題,覺察生活在高雄的人的因為缺水所反應出的生活景況,作品《兩個太陽-菱角?芋頭?》是藝術家將居民買水遺留的水桶廢棄物作為材料,並在水桶中插著一支支金屬製的芋頭、菱角葉標本,在磁浮機械的作用下,金屬葉片如同被仿擬的植物,呈現出在田野中自然搖擺的狀態。此作品反映出對地方研究的關懷,從自然問題、人的應對生存法則、再到廢棄物的利用,無不展示出人與自然共存的張力與倫理課題。

廖浩哲作品,展覽現場,攝影:蔡青樺。
而最具哲學意味的,或許是由廖浩哲所使用的永生苔蘚——它被完好地控制在綠意盎然的狀態中,成為一種被標本化的人工「永生」自然,好似象徵著人類將自然打包進文明系統中的野心,同時也讓人反思這類被人造的自然背後,是否隱含對遠古自然樣貌的遺失與惆悵。
這些作品既各自成章,也彼此呼應,構築出一個既人造、又自然的混種景觀。同時緊扣著我所讀到的命題:如何觀看人與自然共治的時代,以及策展人所欲貫穿的宗旨:「文化化的自然如何在今日作為關照人類與自然關係的媒介」,藉由這檔展覽闡述著經由文化所包裹的自然,並非原始存在的自然他者,反而進入了被觀看與思考的共創語境當中;而這些混種後代(藝術作品)則調節了我們對自然/工業的二元關係,人類面對自然的和諧想像,成為閱讀這檔展覽的關鍵路徑。最後,我想《人.造自然》不只是描繪出藝術家對自然的再現,而是綜合機構關注的議題、策展人的想像、與藝術家的創造,共治出自然在人類社會中的再詮釋,也意味著自然在文化與藝術的運作中產造的新生命。